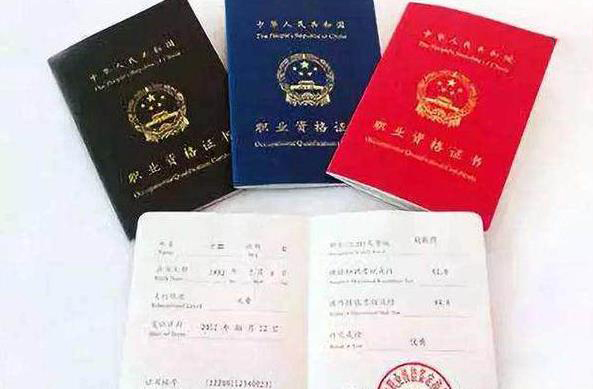我妈总是说自己童年不幸,说感觉自己心理有一些问题,但从未找过心理咨询师,这是什么原因?她童年生活环境确实不好,但情绪不稳定和过于紧绷给身边的人造成了压力,最终还以原生家庭不好为由为自己开脱,这是什么原因,该怎么办?
在我们工作室里,类似的情况真的见了太多——当事人反复说“我小时候太苦了”、“我心理肯定有问题”,可亲友一提找心理咨询师,他就各种推脱。这种矛盾,真的让人又心疼又无奈。
案例中的主人公反复诉说自己的童年不幸,这本身就是一种“呼救”。那些痛苦的记忆,对她来说既是难以愈合的伤口,也是当下唯一能用来表达“我不好了,我需要被看见、被理解”的信号。
她可能隐隐约约真的觉得自己“心理有问题”,但不知道除了反复说,还有什么别的途径能得到帮助。她潜意识里可能觉得,说出来,就是寻求帮助的唯一方式了。

那她为什么就是不肯走进咨询室呢?这背后原因很复杂,也很深。
走进咨询室就意味着要做出改变,而改变意味着要重新去触碰那些深埋的伤痛,这个过程太痛苦了。相比之下,待在自己熟悉的“受害者”角色里,虽然也痛苦,但至少是“已知的”、“可控的”。且咨询带来的未知改变,可能让她更害怕:“万一咨询了也没用怎么办?”“万一我变得更糟糕怎么办?”这种对未知的恐惧,常常大过对现状的痛苦。
另外,社会上对心理问题的病耻感依然存在。寻求心理咨询,对有些人来说,等于承认自己“有病”、“不正常”、“太矫情”。她可能害怕被贴上这样的标签,或者担心家人亲朋会因此用异样的眼光看她。她反复诉说,可能是一种“曲线救国”的求助,但直接去咨询室,需要克服巨大的羞耻感。
还有一点很关键,就是她可能对“被拯救”抱有一种渴望,同时也伴随着深层的无力感和不信任。她可能试过一些方法(自己都没意识到),但没效果,或者听说过一些负面的例子,让她对咨询能帮到自己彻底失去了信心。她可能会觉得“没人能真正理解我”、“说再多也没用,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”。这种绝望感,是她迈出那一步的巨大障碍。
至于她总把“原生家庭不好”挂在嘴边,这其实不难理解。当一个人深切地体验到童年的不幸,并且这种不幸确实塑造了现在的自己,用“原生家庭”来解释一切,是一种自我保护。它能帮助她理解“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”,也能部分地免除自我指责——“不是我自己不好,是当初的环境太糟糕了”。这种解释有它的道理,是自我认知的一部分。
但如果过度使用这个解释,甚至把它作为一切现状(尤其是情绪不稳定给身边人带来的压力)的“万能挡箭牌”,这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回避现实责任的借口。比如,当情绪失控伤害了家人,一句“都怪我原生家庭不好”,潜台词仿佛是“所以我就是这样了,改不了,你们得忍着/理解我”。这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、孩子式的防御机制,就像小孩子犯错后会说是“椅子绊倒的”,把责任推给外部。

作为咨询师(或者作为她关心的人),面对这种情况确实很耗神。我们很想拉她一把,但她似乎把自己裹得紧紧的。这时候,可能需要调整一下思路和策略。
新概念心理专家荣新奇教授指出,最重要的是先放下“一定要立刻改变她”的执念。她的思维模式是经年累月形成的,改变需要时间和契机,强求不得。你的焦虑和挫败感,即使出于好意,也可能被她敏感地捕捉到,反而让她更有防御心,更觉得自己“不被理解”。
当她又开始诉说时,试着先把“怎么又来了”的烦躁放一放,去听听她话语背后,那份未被看见的痛苦、未被满足的需求(是被理解?被安抚?被重视?)。你的稳定陪伴,即使只是安静地倾听,本身对她就是巨大的支持。当然,这很消耗能量,所以你要照顾好自己。
可以尝试一些“软入口”。比如,在她情绪相对平稳时,聊聊你看到的、觉得可能对她有帮助的书籍、文章或视频,不提“心理咨询”,只说是“信息”或“故事”;或者,分享一些简单易行的情绪调节小方法,邀请她一起试试,就当是娱乐放松。目的是让她接触到这些方法,而不是强推。
同时,也要在“理解”和“设立边界”之间找到平衡。你可以表达理解她的痛苦“听你讲这些,我能感觉到你小时候受了太多苦,那种无助感一定很强烈。”但也需要温和地表达她的某些行为对你或家庭氛围的影响,比如:“妈,有时候你声音突然提高,我会感到特别紧张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这比直接说“你脾气怎么这么差”要容易接受得多。并且,可以为自己的感受设立一些边界,比如希望她在生气时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

有些人,带着如此深刻的创伤和固化的模式生活了这么多年,改变对他们来说可能异常困难,甚至他此生都无法真正走进咨询室去直面那些伤痛。
这时候,你可能需要思考:如果他就是“不改变”,你如何在这个关系中,找到一种对自己伤害更小、更能承受的方式去相处?这可能涉及到你自身对关系的期望和互动模式的调整。
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他的痛苦是真实的,你的困扰也是真实的。当感到超出自身能力范围时,寻求专业的帮助或支持对双方来说,都是明智且重要的保护。
有时候,陪伴一个人走过他最黑暗的路程,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治愈力量。